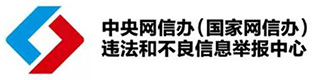民间借贷出现“黑白欠条”应引起重视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充分保护人民群众和广大民事主体在民间借贷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资金融通秩序,最高院结合审判实践,经审判委员会五次专题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系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将民间借贷涉及到的重点难点再次推到社会关注的焦点里。此次《规定》对1991年的《司法解释》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借贷利率划出了年利率24%和36%两条线,分出三个区域,改变以基准贷款利率四倍作为利率的保护上线。
由于金融业和法律系统相对不健全,民间融资长期不规范,风险难控,实体经济金融需求比较强烈,使得涉及高息借款愈加突出,高息的隐藏手段也愈加隐蔽。随着民间借贷案件新情况、新特点的出现,民间借贷案件日趋复杂,审理难度也日益增大,以下为法院审理案件中,遇到的几种新型高息借款隐藏手段,旨在提醒人民群众加大对民间借贷法律风险的自我防范,全力维护全市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黑白欠条”案件
张某因李某欠其44万元借款未还,将其诉至法院。在开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发现,张某所述44万欠款仅有20万元的银行转账凭证为证,其余24万元无其他辅佐证据证明其借款事实。张某称剩余24万元以现金方式借给李某,并无其他证据可以证明。介于案件证据来源不明确,本案审判人员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详细询问,并说明作伪证、构建虚假债务的严重后果。李某终于承认事实,称剩余24万元为借款利息。他实际出具两份欠条,一份欠款44万元用于李某起诉,另一份20万元欠条为他们私下真实借款依据。
民间借贷由于交易的隐蔽性往往成为虚假诉讼的高发地带,包括债权人虚增债务、债务人恶意逃债和借贷双方虚假诉讼。虚构借贷关系真假难辨,双方当事人在涉诉构建虚假债权债务关系的行为必须受到法律严惩。
“房屋买卖协议”案件
代某将李某诉至法院,称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后,其已付款20万元,但李某不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请求法院依法判令房屋过户。庭审过程中,代某提交双方真实签名的购房协议书、银行付款凭证、协议公证书,预告登记等多份证据,购房要件非常完备。但审判人员发现,李某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出卖,并且在庭审中答辩其与原告之间实属借贷行为。他们之间签有欠条,约定高息,房屋是用于抵押。
民间借贷实践中并非单纯的出借资金,而与其他类型纠纷案件相互交织的情况逐渐增多。以房屋买卖协议形式来隐藏高息借款行为,在本院受理的房屋买卖协议案件中出现多次。此类房屋买卖合同目的在于担保高利贷本息,而不是出售房屋所有权。因法律禁止抵押约定抵押物所有权转移,为使担保合法化,高利贷双方选择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以合法形式掩盖真实法律关系。
“综合费用”案件
张某与某典当行签订合同借款10万元。违约后某典当行诉至法院请求判令偿还借款10万元及利息、综合费用、逾期综合费用。本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贷款合同约定利率并未超越法律规定,但在“综合费用”一项显得很蹊跷。综合服务费计算方式与利息一致,并且利率比利息计算利率更高。
由于法律对借款利息不得预先在本金中予以扣除作出禁止性规定,但是对于综合费用预先扣除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对于综合费用是否属于法定孳息还存在争议。因此,典当行内的按照行规,在综合费用一项中约定高息并且预先扣除显然是一种变相的高息借款行为。
“跑跑”案件
民间借贷案件呈现更大特点是欠款人经常“下落不明”,债务人“跑跑跑”。债务人消极应诉或下落不明,都将给法院送达带来困难。若以公告送达进入诉讼程序后,又将面临审理问题,即只有债权人一方陈述举证,法院无法听取双方质证意见及陈述,加大了辨别虚假诉讼难度。若依照程序作出缺席判决,给执行工作也带来困难,借款人最终的债权也无法实现。
2015年至今年8月,基层法院共受理民商案件1858件,其中民间借贷案件占16.89%。其中城区法庭今年受理立案的243件案件中,民间借贷纠纷占23%。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大幅增长,已经超越婚姻家庭案件成为民商事第一大案件类型,案件主要特点呈现为涉案主体多样化,标的额迅速增长,高息现象普遍。
2011年,山东邹平县各个高利贷金字塔瞬间崩塌,村民们的暴富梦一夜破灭。温州多家担保公司垮塌,资金链断裂企业频频倒闭,使得温州陷入极度恐慌和焦虑之中。2011年以来,全国民间借贷危机可谓此起彼伏,除温州、鄂尔多斯外,江苏贫困县泗洪、陕西神木、河南安阳等地也均出现危机。大量事实告诉我们,民间借贷一旦崩盘,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如何实现民间借贷的软着陆,将民间借贷纳入法治轨道已经刻不容缓。基层法院将围绕“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工作目标,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严厉打击非法集资行为,不断规范民间融资秩序,为促进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