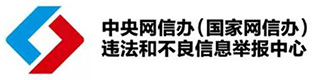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研究问题探讨
人民法院内设机构改革研究问题探讨
曾都区人民法院 朱妍
论文提要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司法改革进行了顶层设计,包括法院行政化等司法顽疾均有所触及。司法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一发而动全身,要推进司法改革需要进行了大量的资料梳理和理论引进,及经验总结。法院内设机构的改革在以往三轮司法改革已经取得了部分成效,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本文以法院内设机构的改革进行回溯,对当下法院内设机构配置进行实证分析,以期对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进行检讨和构想。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法院内设机构追溯,包括人民法院组织法的立法配置,三轮司法改革的举措和成效;第二部分是目前内设机构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成因的探析,第四部分是完善进路与一些粗浅的构想。
一、法院内设机构配置及改革追溯。
1、《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法院内设机构的配置。1980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以下简称《法院组织法》)是新中国首部关于法院内部人员如何组织的宪法性文件,要对法院内部组织——内设机构研究,就必然无法绕开这部纲领性法律。根据《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的内部组织由法律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人民法院的组织由法律规定。据此,《法院组织法》对人民法院的内部组织安排首次进行了整体性的界定。根据《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包括最高法院在内的各级人民法院可设置刑事审判庭、民事审判庭、经济审判庭,中级以上的人民法院还可根据审判工作需要设置相关的审判庭。由此观之,《法院组织法》对法院内部人员如何组织,法院内设机构如何配置,规定的非常简陋,并留下了一个兜底条款给各级法院充分发挥的空间。实际司法实务中,各级法院的内设机构已经远超《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大量的审判监督庭、立案庭及行政庭等审判业务庭均游离于法律之外。一方面,这是因为《法院组织法》制定之时,依法治国建设刚刚起步,行政诉讼法、著作权法等大量法律均还未制定与实施,这些审判庭当时并未成立,因而从当时来看,《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基本上还是契合了审判实践的。另一方面,法院组织法最后还预留了一个兜底条款,即中级、高级法院均可根据工作需要设置其他相应的审判庭。
2、司法改革后法院内设机构配置现状
经过三轮的司法改革,人民法院的内设机构配置整体上的得到了优化调整,但局部上也存在未达成改革初衷等问题。三轮司法改革下来,人民法院人民法庭的配置得到了优化,大量的城区法庭得以撤并乃至难觅踪迹,乡镇的法庭得到了优化合并,基本上符合改革纲要的初衷,法警人员实现了编队并集中统一管理,各级法院均建立了执行局,将执行人员纳入专门执行部门实行统一管理,执行局普遍实现了升格,执行人员得到了充实,各级法院都配置司法技术部门和诉讼服务中心,以应对数字化时代下人民群众对司法的新期待和新要求,但专门的司法统计和司法鉴定机构并未建立,司法统计仍然配置在各级法院的研究室等综合审判业务部门,法院不再受理司法鉴定,而是由司法技术部门统一管理并授权社会有权机构进行委托鉴定。大量的少年法庭得以建立,但少年法院至今未见雏形,审委会实现了专业化的分类改革,大部分法院均分设了刑事审判专业委员会和民事行政专业委员会,铁路法院、石油法院等专门法院划归地方法院,纳入最高法院统一管理下的人民法院组织体系。
二、法院内设机构存在的问题
法院内设机构配置及其改革应当遵循促进司法公正与提升司法效率的追求和旨趣。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各国法院的永恒主题。因而,要判读法院内设机构是否科学合理,法院内设机构改革是否得当,主要当以公正和效率两大指标予以评析。但综合历时性数据与共时性展开,我们发现,法院内设机构数量越来越多,法院内设机构规模越来越大,并不利于提升司法公正与效率。具体分析如下:1、机构数量不断增长,机构规格不断抬升,非审判机构增长迅速,机构规模不断膨胀,高级法院内设机构平均值达24个;机构规格不断提升,政治部、执行局均实现了整体升格,湖南高院还成立了立案信访局,为副厅级建制,比一般的内设部门高半级;机构规模不断膨胀体现在,很多内设机构如办公室、执行局等部门因人员庞大、事务繁杂,内部还设立了文秘科、裁决科等三级机构;非审判机构的数量不断增长,有的法院如新疆高院甚至超过了审判机构的数量。导致审判部门与非审判部门的比值日趋下滑,大量的编制被非审判部门挤占,相当部分具备审判职称的法官在非审判部门从事与审判无关的司法行政工作,大量法官资源的限制,进一步加剧了案多人少的矛盾,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升。
2、机构设置不统一,混乱无序,有损司法严肃和法制统一,侵蚀司法权威,从法院内设机构配置来看,法院的内设机构存在设置不统一、混乱无序的问题。很多法院为解决干警晋升等问题而根据“本地区工作需要”设置了别具特色的如院志办、基层办、基建办等五花八门的部门。这些部门的设立,法院组织法等法律并未授权。即使是同一个部门,各地法院的职能与权限亦是不统一的。如传统的民事审判一庭,有的法院受理婚姻家庭等传统民事案件,而有的法院则是受理房地产等经济案件,这不仅不利于法院的整齐划一,有损司法严肃,而且给当事人诉讼造成困扰和不便,不利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因人设岗,因需设岗增加机构、部门显然容易导致增加管理层级,加大管理难度,不利于司法信息的传递,不利于案件的快速高效流转和办结,亦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升。
3、法院科层制管理模式进一步固化,陷入行政化的泥潭,有悖于法官职业专业化的特点,不利于法官素质的提升法院行政化的顽疾历来为学界和律师所诟病。在我国法官并非一个专业技术性职业,法官并不特别强调专业知识积累,而是更注重政治方向的正确,一名科班法律毕业生要成为法官,需要通过公务员考试。即法官不是按照自己的职业特点构建一套职业准入机制,而是等同于一般公务员纳入公务员体系管理。各层次的法官亦有相对应的行政级别,因此自然产生了相应的科级法官、处级法官等。法院行政化不仅体现于此,还广泛分布在法官的周遭,包括法院内部的行政化,承办法官的裁判文书需要庭长、院长的层层签发方可下判;包括法院外部的行政化,法院上下级的指导关系已经严重异化为行政管理关系。虽然法官法规定法官的工资福利由法律另行规定。但迄今为止,并未有相关法律对其进行界定。因为陷入行政化的泥潭,法官要想获得更高的工资福利待遇就必须进行职务级别的晋升,而不是注重于司法知识和审判经验的积累。自然,法院内设机构增多,机构负责人和副职就增多,有利于满足法官对行政职务和行政级别的追求,自然法院内设机构增多,增设机构副职对法院系统来说是一件皆大欢喜的事情。因此,为经济上的生产自救,满足法官对行政职务和级别的追求与需要,法院机构膨胀非常明显。
三、法院内设机构的成因与检讨
1、法治国建设的逐步推进导致法院收案数连年攀升,案多人少的矛盾愈发突出,法院人员、组织规模迅速扩张导致法院内设机构不断膨胀,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逐步确定为国家战略,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逐步增长,诉讼费的降低诱发诉讼门槛的降低,大量新法的出台与实施,导致法院收案数激增,这个可以从全国法院历年收结案数加以佐证。以最高法院启动一五司法改革的元年--1999年为例,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共受理各类一审案件541万件,而到了2014年,最高法院周强院长在年度工作报告提供的同项收案数据已激增到1421.7万件。法院收案数的激增是多种原因力交织而成的。一方面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逐步推进,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与完善,包括著作权法、专利法、物权法等一大批新法的生效实施。另一方面是民众权利意识的高涨,越来越多的公众利用法律——诉讼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在处于转型期的当下中国,大量的社会矛盾以诉讼的形式涌入法院导致法院收案数激增,此外法院诉讼费的降低导致诉讼门槛的下调,部分当事人滥诉等亦起了催化作用。这些原因力的合流导致法院收案数的暴增。法院收案数的激增必然激化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导致各级法院的不断增编致使法院组织规模愈发庞大,人员增多,必然导致法院管理层级增多和内设机构的扩充。为满足管理的需要和畅通法官职务晋升通道,一方面是法院大量的知识产权庭、金融审判庭等新型审判庭的增设,另一方面三级机构的增设以便管理,而且审判业务部门增加必然诱发审判管理部门如审管办和审判辅助部门如司法技术处等部门的增加。法院内设机构的膨胀,三级管理机构的增设等多种原因汇聚成原因束致使法院整体机构的膨胀。2、法律规定滞后,与社会发展和时代要求脱节,缺乏可操作性,导致法院内设机构设置混乱,名称不统一,损害司法权威。检读现有的法律体系,关于法院内设机构的设置主要由《宪法》和《法院组织法》规定。现行《宪法》的规定过于宏观,而《法院组织法》对法院内设机构的配置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包括最高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并且在每级法院的收尾都运用了兜底立法技术以补充前述的规定。但是翻检《法院组织法》,我们却发现法律对各级人民法院内设机构的配置规定非常过时,已经远远脱离时代的要求,该法的规定已经远不能满足现实的司法实践需求,与现有的内设机构配置现状严重脱节。如随着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一批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实施,全国绝大部分中级法院乃至部分基层法院均已设置了知识产权庭,但《法院组织法》却未对此作出有力回应予以相应的调整。不仅如此,审管办的设立,也是缺乏基础的前提下,由各地法院先行探索,最后由最高法院下通知、文件在全国各级法院统一推进。不宁唯是,各地各级法院很多机构的设立、升格均主要由此类最高法院的文件、通知推进,而非法律的授权。此外,《法院组织法》对内设机构的设置规模、规格、级别均未作出详细、明确的可操作性规定,导致各地各级法院对内设机构的配置混乱不堪局面。如由于法官无法定额,自然各地法院人数非法定,法官规模也非法定,而是存在浮动空间的,那么各审判部门的法官员额分配也无法明确。法院内设机构规模几何、规格几何,即使是一个大致的标准,《法院组织法》亦未对此作出相应的立法回应。由于法律的缺位,各地法院机构的设立与否、升格与否、规模几何有赖于各地法院院长的资源获取能力,依赖于各地贯彻最高法院文件、精神的力度,依赖于各地法院所在地方党委、政府对法院工作的支持力度。即使是同一个部门,很多法院的职能或名称亦不尽相同。如绝大部分中级法院的知识产权案件受理、审判设在民三庭,而有的法院如深圳中院则干脆直接命名为民三庭,而有的法院则配置在民四庭。即使是同一个名称的部门,如笔者所在法院的民一庭主要受理婚姻家庭、道交事故等传统民事案件,而辖区内的法院则有的却受理经济案件。这很容易误导当事人,给律师代理案件也带来一些不便。法院是一个严肃和神圣的地方,其内设机构的配置,包括名称、受案范围、机构规格也当尽力实现统一化,应当由法律规定,以确保司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3、法官法未能有效落实而沦为睡美人,法官单独序列的工资福利至今未能兑现,导致法院陷入行政化的泥潭。为满足法院内部人员的晋升需要,大量法院增设机构、扩充规模,升级规格,致使人员膨胀,机构臃肿,无法满足司法公正与效率的旨趣。关于法官工资福利待遇的问题,《法官法》拿出了专章——第十二章进行专门阐述。根据《法官法》的规定:法官工资根据其审判特点,由国家规定,且实行定期增资制度。但迄今为止,国家并未出台法律落实《法官法》关于法官工资福利单列,体现审判特点的工资序列和标准。而因《法官法》沦为一纸空文的睡美人,实践中法官的工资还是参照同地区其他公务员标准。既然如此,法官工资福利并未体现其审判行业的特点与属性,而是与其他公务员并无二致。在同级机关,法院相比于党委办、政府办等政府组成部门、内设机构,人数庞大,自然晋升非常缓慢和困难。而且参照行政化的科层制机关管理模式,法官的工资福利等待遇全部与其职务、级别相挂钩,相比于政府部门其他公务员,法官对职务、级别的需求同样强烈。而在《法官法》未能落实的现实情境下,法院系统采取了集体“生产自救”的方式,即增加人员——增设机构——增配副职——升格机构等一系列方式以满足法院内部人员、法官的日益增长职务晋升需求,以缓解晋升压力,提升工资福利待遇。
四、法院内设机构配置的改革构想。
1、优化诉讼程序,减少诉讼案件,压缩法官规模,从源头上遏制法院人员膨胀,机构膨胀。法院机构膨胀首先是人员的膨胀,人员的膨胀直接导致机构臃肿,由于人数的增多,法官的内部管理需求异常强烈,导致需要不断增设机构、下设三级机构,以分摊管理规模,分解管理任务。而人数的增多的首要源头便是案件数的迅猛增长。由于人员的增多,不增设机构,实现专业化分工,案件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出现一两百人的超级内设机构,无疑不利于法院管理。根据前述的分析,我们知道晚近十年,中国法院受案数连年攀升,而法院诉讼案件的迅猛增长直接导致引发案多人少的矛盾,为缓解办案压力,确保司法质量,各级法院都采取了增加编制,扩充法官规模这一措施予以应对。法官规模的扩充,直接导致法院人数的急剧膨胀,要应对如此庞大的司法人员管理任务,增设机构无疑是个好办法,因为增设机构不仅能够分摊管理任务,降低管理难度还能增设大量科级、处级法官乃至厅级法官,有利于拓宽法官职级晋升渠道,缓解法官的晋升需求,以提升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因此,要解决当前法院机构膨胀的问题,首要的措施便是降低诉讼案件,以压缩法官规模。而降低诉讼案件数显然不能通过提高诉讼费抬高诉讼门槛等办法,只能加大人民调解力度,从总量上降低受案总数,实现专业化审理,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单个案件所耗法官数。因此,笔者建议从诉讼外强化人民调解,加大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的指导力度,通过司法确认人民调解效力,让大部分案件通过诉外调解的方式得以化解和分流,缓解法院收案压力。从法院内部来说,应当加大诉讼内调解,将调解方式贯彻运用到诉前、诉中、诉后等诉讼的全过程,以减少单个案件的办理时间,并辅之以专业化审理,扩大简易程序、小额诉讼程序适用范围,通过繁简分流,实现案件的专业化与高效审理以压缩单个案件所耗的司法资源,提高法官办案效率。如此方能既缓解受案压力,亦能压缩法官规模,缓解目前法院内设机构臃肿不堪的难题。
2、修改不合时宜的《法院组织法》,确保目前机构设置符合立法规定。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对全国各级各地法院的内设机构规模、规格、数量、名称、范围等方面予以法定化,统一名称,合并同类,精简数量,以实现瘦身和统一,维护司法的严肃性,确保司法的权威性,以提升司法公信力。根据前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经过三轮司法改革,法院内设机构改革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仍然存在数量繁多、规格不一等问题。而且现有各级法院内设机构的配置已经远超出1980年的《法院组织法》,有违法律之嫌,或者说《法院组织法》已经完全与当前法院内设机构配置现状严重脱节,因此,有必要对不合时宜的现行《法院组织法》有关内设机构配置的部分内容进行全面修改调整,通过立法明确各级法院有权配置的内设机构数量、名称,受案范围,规格,以确保各级法院机构配置的统一化。修改《法院组织法》,应当进行全面调研摸底,并根据各级法院受案数、人员规模进行合理配置,对所有部门的名称、工作职责应当进行统一化标识,尽可能合并同类,精简数量,以确保法院内设机构配置的严肃和统一,维护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
3、落实《法官法》关于法官工资福利单列管理的规定,出台《法官法实施细则》, 淡化行政化管理模式;构建大审判管理格局,实行所有法官随机分案,确保司法资源得以最大化利用。法院行政化问题一直以来为法学界和公众所诟病。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司法改革重启改革大幕,明确要求祛除法院行政化的问题。究其根源,法院行政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法官一直被当做普通公务员对待和处理,而无法享受与审判特点相适应的工资福利,导致法官不满足于办案,而更热衷于追求职务和级别的晋升,以实现个人职业前景。而对此,《法官法》明确规定法官的工资福利待遇应当与其审判特点、工作性质相适应,由国家相关法律予以明确。但1979《法官法》实施迄今为止,空闻下楼声,不见人下来,并未有相关法律予以专门规定。《法官法》沦为睡美人,因此有必要出台《法官法实施细则》以确保法官能够享受有别于其他普通公务员,但却与法官审判工作特点相适应的工资福利,使法官得以专心办案而非热衷于行政职级的晋升,从根源上剪除法官对行政职级追求的内在驱动力,拓宽法官个人的晋升空间,以确保其获得与法官等级相匹配的工资福利,让大部分法官得以专心办案,安心司法这片热土。此外,淡化行政化管理模式,还当有其他措施予以配套,如参照前述成都高新区法院的做法,建构大审判管理格局,实行所有具备法官职称的人员随机分案,消除法院内部部门界限,实行所有法官包括法院院长、庭长随机分案,以解决法院内部忙闲不均的问题,确保法官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和开发,以提高司法效率,确保司法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