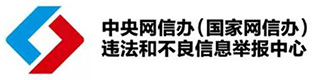儒家“以礼入法”思想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引言
两千多年来,儒家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虽然现代法治思想与儒家法律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冲突,但时代的发展也表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合理成分使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相融合。其中“以礼入法”思想在与现代社会相融合的过程中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产生了极其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一、“以礼入法”思想的概述
儒家法文化“礼”为核心。“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的习惯, 起源于原始人的祭祀。但经过儒家渲染之后, 尤其是经过西汉的发展、扩充后, “礼”被视为根本的国家制度和主要统治方法, “礼, 经国家, 定社稷, 序人民, 利后嗣者也”, “夫礼者, 所以定亲疏,决嫌疑, 别同异, 明是非也”。并且以礼为根据衍生出各种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 这时, 礼的规范相当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法”。“不知亲疏远近, 贵贱美恶, 一以度量断之”, “一准乎礼”。凡此皆可见, 中国古代法律的制定, 完全自觉地遵循、贯彻着儒家法文化“礼”之精神。封建社会是准礼立法或以礼为法, “礼”获得了相当于甚至高于成文法典的法律功能,成为法律实践最根本的原则。
“以礼入法”,始于战国末期,形成于秦汉之际,确立于汉武帝时期,成熟于隋唐时期,完备于宋明时期,一直延续到近代,经历了上千年曲折渐进的发展过程,最终积淀成自成体系、独具特色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形态。其本质上是指宗法制与官僚制的结合,家族伦理原则与君主专制原则的结合,是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的结合,贤人政治与以刑法治国的结合。
二、“以礼入法”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
纵观中国古代 “以礼入法”的发展历程,其主要通过两条途径来完成:其一是立法者以儒家提倡的伦理道德为指导制定法律;其二是司法官在司法实践中引经决狱进行断案。具体而言,“以礼入法”包括四种表现形式。
(一)礼指导法律的制定。在《唐律》制订过程中,纲常之礼乃《唐律》最基本的内容,且以礼改律之处甚多,《唐律》的制定与修撰主要以礼为指导。
(二)礼直接入律。《唐律》中,部分律文几乎为礼之翻版。例如《名例律》之“八议”乃《周礼·秋官·小司寇》“八辟”直接照搬。《唐律疏议》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一准乎礼”,其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完全依照礼教,如“八议”、“五服”、“同居相隐”等等。
(三)“礼为先,律为后”的司法原则。审判实践中,以礼折狱,弃律从礼的案例甚多。司法官员遵循“礼为先,律为后”的司法原则,“宁可不依律,万不可违礼”。
(四)礼法互补。礼侧重于预防犯罪,“禁于将然之前”;法侧重于惩罚犯罪,“禁于已然之后”。例如唐代凡律无明文规定,均可参考律疏处理。实际上,律疏仍是以礼为理论基础来弥补法律条文的不足。
三、“以礼入法”思想对现代法治的影响
(一)“以礼入法”思想对现代法治的消极影响
1、礼乐教化深入主动引导人性与厌讼导致人格畏缩。在儒家看来,道德和礼仪是社会秩序最根本、最深入的解决手段。“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而以此同时,儒家精神从根本上是厌讼的。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叔向曾经认为“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弃礼而征于书。孔子也说:“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儒家认为,倘道之以礼,争端是易于解决的,这种观点使儒家产生一种偏激——既然事实上“没有两种相同的情况”,故试图将所有可能的情形归纳于某种一般化的法律范畴之下这种做法持怀疑态度。而在儒家学说和理论的倡导下,厌诉成为中华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厌讼造成后果首先是个体缺乏直面权利的勇气而至人格的对内畏缩和坍塌,崇尚道义贬斥利益的谦让、息事宁人、明哲保身生活方式已然成为传统社会生活的常态,个体在秩序社会中争取权利和利益的人格受到压抑和克制。其次,由于对于权利的压制和忍让导致中国传统社会保护个体权利和尊严的法律价值的停滞不前。最后法律权威对个体的积极影响也由于长期缺乏社会大众的广泛生活实践体验而长期软弱无力。
2、天理、国法、人情的价值融溶与纠缠。在儒家伦理中,人情最典型莫过于现世社会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百姓心中的天理其实就是三纲“王道之三刚,可求之于天”,法也是天理的表征。朱熹《集注》云:“法者,天理之当然者也。”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使法制的观念获得了完备的合理的理论和伦理基础。但是,三者的含混纠缠同时也使法治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受到抑制。首先其使得传统社会活中法制的运行产生巨大的不确定和对象的区别性。从而使传统法治规范缺乏对个体行为后果的可预测性,为“人治”的合法性从理论上制造了依据。纠纷的裁决是依靠、道德、伦理、裁决者本人的自由心证而不是法律的文本,合“礼”即合法。“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违于法者诛”这与现代法律规范的普适性、一般性、规范性相冲突。其次,缘“情”的道德与法律的混合使具有强制力的传统社会法律对于个体要求标准过高,而难于遵守,导致法律等同虚设。最后法律的适用过于强调道德和伦理的应用而排拒文本的规范的刚性从而导致法律的规定缺乏权威。
3、儒家礼治的根本在宗法制,以等级制、亲属关系为社会组织架构的基础,其尊卑、贵贱、长幼各有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稳定与否。
在宗法等级制中,法律强调国家本位主义,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从而忽视个人权利,否定人作为社会主体的存在。法律仅仅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种工具,体现少数人意志并只为少数人服务。从刑罚制度上看,在等级秩序下产生的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现代法治以平等、自由为基础,人们平等地受法律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体现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尊重和保障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是现代法治追求的目标之一。礼是差别性规则,法则是同一性规则。“以礼入法”导致人们权利本位意识单薄,
(二)“以礼入法”思想对现代法治的积极影响
1、“以礼入法”——正义法律的道德基础。儒家法律思想中的道德价值的融入代表了中华法治文明的智慧。“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法律和道德是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不可或缺,互为补充的两方面。“以礼入法”的价值体现在:首先,立法时法律的正当性基础。道德是法律权威的最为根本来源即其立法时的法律价值,尽管规范论者曾经主张法律是主权者的命令,“恶法也法”,但是自然法论者的思想和理念,最容易触动社会大众的守法意识和引发守法行为的共鸣。其次,在执法过程中,法官和执法官员的自由裁量权行使的权限范围内,道德始终是法律规范价值的主宰。最后,法律价值的提升和进步始终是以社会的道德进步为推动力的。
2、儒家法文化“以礼入法”的思想主要强调犯罪的综合治理, 即将犯罪预防和犯罪控制统一起来。通过发展经济、教化等一系列措施来预防犯罪, 使犯罪得到控制; 通过对已有犯罪的惩罚来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以礼入法”思想的重要内容——“防患于未然”的法律思想, 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仍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首先, 从经济上预防犯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现代法治建设是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经济的发展对于预防犯罪有根本意义。如若不能“仰足以事父母, 俯足以蓄妻子”, 就会“穷则变”的现象, 即当人的基本物质需要得不到满足时,往往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儒家法文化中的这一具体思想和现代法治建设的进一步结合就是要求大力发展经济,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同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以保障最低生活水平, 从源头上消灭犯罪。
其次, 从思想上预防。其重要体现就是“教化”思想, “教之”、“驱而之善, 故民之从之也轻”。在今天, 也就是要求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前提下加强普法宣传工作, 使人民知法、懂法、守法, 通过思想教育和法治教育, 避免犯罪的发生。
第三, 从刑罚上预防。儒家在“德治”、“仁政”和“教化”效果不明显的情况下极力主张用刑, 注重通过刑罚的惩罚性和威慑功能来预防犯罪“起法正以治之, 重刑罚以禁之”, 即“教而后诛”。通过给予犯罪分子相应的处罚, 一方面对其心理产生威慑作用, 使其不敢再犯; 另一方面, 也对社会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 使其他人不敢以身试法。
“以礼入法”思想将古人“标本兼治, 重在治本”的朴素辩证法运用于国家治理之中, 符合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 具有调动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各方面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的特点, 比较容易取得长治久安的积极效果, 对于安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3、儒家法律思想中融入的道德价值代表了中华法系的文明与智慧。“徒法不能以自行。”从古至今,法律和道德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不可或缺、互为补充的基本要素。儒家道德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首先,儒家法律思想中的道德价值精华可作为法律正当性的立法基础或参考。对许多国家来说,重要和基本的道德规范一直都是法律来源之一。从一定意义来说,如果没有对道德理想和价值的追求与体现,法律就有可能成为专制与奴役的工具和手段。其次,道德是执法以及自由裁量权行使的价值范围或标准之一,是人们守法的价值导向。法律不能穷尽社会生活,也永远滞后于社会生活,当法律不能直接明确地面对社会生活时,道德规范和道德价值可起有效弥补作用。最后,法律价值的提升和进步始终是以社会道德的进步作为推动力的。儒家引礼入法、礼法互补也即道德法律化并非一无可取。法律与道德的调整对象往往是重叠的,同时发挥两者的作用也是规范和治理社会的必然选择,正如“依法治国”背景下也需要“以德治国”之道理。
四、结语
儒家法文化中的“以礼入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古代社会影响至深。在近代虽然遭到了一系列的冲击, 但经过长期的发展, 已积淀为民族的法文化心理结构, 并且这种心理结构已成为民族在法律方面的个性, 其中的积极因素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的组成部分,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志富 陈艳.儒家法文化的现代法治价值[J].武警学院报,2006,(10).
[2]王鹏飞.古代礼法结合的治国思想及启示[J].理论探索,2007,(3).
[3]张成铁.和谐社会法治精神的发掘与锻造——儒家文化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与整合[J]. 法治与社会,2008,9(上).
[4]高琳.儒家礼法结合精神及其现代价值[J].法治与社会,2009,5(上).
[5]赵庆鸣 喻惠贤.略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与融合[J].创新,2011,(2).
[6]蒋璟萍.礼仪的伦理学视角[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95~106.